2020红米K20 PRO街拍作品 伟大的街拍时代已成为过去?
6月4日,飘在思密达整理发布使用红米K20 PRO拍摄的近期首尔街拍。
捕捉时代与世界广泛而深刻的一个断面,或者带着自己的主观与标签捕捉他人整个人生的一个瞬间并向世界展示,街头摄影是艺术还是欺骗?
日本街头摄影师铃木达朗(Tatsuo Suzuki),通过拍摄东京及全球大城市街头风景的照片,最近在世界闻名。他多年来被选定为富士胶片的品牌大使,明年初还将在“摄影家的圣地”全球顶级摄影图书的出版帝国史泰德(Steidl)出版作品集。但是最近他多少卷入有些不光彩的争议中,富士胶片公开的铃木达朗新产品上市纪念使用后记视频引起了公愤。这位摄影师拍摄大片的主要方式是用广角单镜头靠近被摄体上贴身拍摄,几乎冲进拍摄对象怀中。在拍摄完后,他便转过身从容离去,不少人对他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声讨。这并非老生常谈。声讨不知有多么强大,富士胶片必须将相关影像和项目结果全部销毁,并上传道歉文。当然,铃木达朗也必须从富士胶片的品牌大使位置上退下来。
但是,韩国摄影作品集专业书店IRASUN的运营者兼美学家金振荣(音)在搜索铃木达朗照片的过程中,始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种程度的作品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倒不是说他的作品看起来很清白,只是人们的反应有些夸张。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在填满IRASUN的着名摄影集中,有一半应该重新考虑伦理性。因为Street Photography和Candid Photography(在拍色对象尚未确认拍摄与否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是当今摄影艺术的一大轴心。“缺乏尊重的工作方式和对行人面部特写的结果好像引起了公愤”,金振荣代表立即从IRASUN的书房中拿出两本书回到座位。20年间拍摄的世界各地的类似路人穿戴的Hans Eijkelboom《Peopl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和突出纽约行人头像的Philip-Lorca diCorcia《Heads》。前者是将照相机藏在大衣里,从口袋里按快门来拍摄庞大的人员,没有引发争议;后者被一人提出了巨额诉讼,但最终在大法院得到了胜诉判决。金振荣表示,“并不是不能理解人们的反应,因为我也不喜欢被拍到。只是偶尔会想,人们是不是认为肖像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认为在公共场所被某人的照相机拍到本人的脸是一种侵害,则有些过分。去公共场所本身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排他性。”
金振荣再次委婉地表示这只是她的想法,但实际上她的见解和美国纽约州律师Kathleen E. Kim的法理见解几乎一致。整理有关艺术的法理和案例的《艺术法》的作者Kathleen E. Kim律师表示,韩国摄影家们异口同声地吐槽狭窄的活动空间。她表示,“我们的社会对肖像权非常敏感,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肖像权的特别法律。与隐私权和著作权有很大距离的肖像权也是韩国特有的概念,肖像权诉讼是以宪法中明示的‘人格权’为根据的。因为没有法律,各级法院也会出现不同的判决。如果普通人也不经过同意,自己的照片被利用在商业上或证明名誉受损,就有可能胜诉。但仅仅凭不喜欢在公共场所被拍到是很难的。”肖像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过度的权利。当然,法律并不是在任何环境中都通用的千古不变的真理,而是各社会成员达成的有关价值观最起码的协议。那么根据重视肖像权的国内舆论,我们的法律会不会向着限制在公共场所拍摄的方向发展呢?Kathleen E. Kim回答说:“虽然有这这样的要求,但很难实现。”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为了躲避狗仔队发生事故死亡时,美国和英国曾经试图制定防治狗仔队法,但这一切都被搁浅了。如果不想制约表现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就必须明确哪些地方是违法的,哪些地方是合法的,但很难找到合适的标准。高丽大学法学院教授朴景信更进一步表示,不能接受用法律制约Street Photography。他说道:“一个陌生人进入他人的私有财产领域就会变成入侵。也就是说,公共场所是两名陌生人可以轻松见面的唯一的空间,扩展我们的社会生活。比如集会、示威、广告都有公共场所的存在才变得可能,政治、经济等没有公共场所的概念是不可能实现的。今后我们需要保护公共场所的自由,记录和共享眼睛看到的东西的自由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有与此相反的观点。《德国肖像权理论与事例》的作者、媒体仲裁委员会教育本部长李秀钟(音)教授认为,这种观点依靠美国国内的案例,是过于自由主义的解释。肖像权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都非常重视,从德国法律中引入多数主旨的韩国法律也倾向于此。他表示,“当然,如果认为时事领域较大或对艺术利益有贡献,法庭就会站在摄影师的一边。但这只是例外的认定,肖像权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侵犯的,是保障人类尊严的人格权之一。它的原则是每个人的形象是否向大众公开,只能由自己决定。无论是谁,都不能主张‘我是从事艺术摄影的摄影师,所以可以在街上拍摄任何人的照片’。”在艺术摄影领域的肖像权纷争中,很难找到摄影家败诉的事例。对此,李秀钟分析说,与报道摄影和以商业目的摄影相比,诉讼数量本身还不多,因此引发这种错觉。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肖像权成为社会问题,形成新的舆论只是时间问题。他指出,“韩国也有必要在此之前将肖像权的相关规定进行得更政治、更仔细的修改,将人格权纳入我国民法的尝试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也应该尽快实现。”
拥护Street Photography权利的声音中,不仅仅包含“表现的自由”这一大义。想要通过法律加强在公共场所的摄影权的法国前文化部部长奥雷莉•菲莉佩蒂(Aurélie Filippetti)提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与下一代共享摄影家对世界的看法。记忆可能被歪曲,如果没有照片,我们的社会就无法拥有一张脸。”照片是艺术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理解社会的主要史料。在世界85个国家旅行时留下街头作品的摄影家K. Chae将街头摄影称为“面向未来的照片”。他表示,“我认为街头摄影才是可以将现代生活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媒体。即使通过演出的照片很好地反映那个社会,其层次也不一样。如现代的表达青春的照片全部来自Ryan McGinley,想想一下,是不是很不幸呢?真正的青春不是脱光在大自然中奔跑的样子。”虽然K. Chae在商业摄影和非商业摄影等多种领域活动,但他总是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规定为“街头摄影师”。只是在谈论街头摄影师的美德时,就像要强调其美德一样,其前提是其美德只有在摄影家各自对照片伦理的不断的提问下才能发挥作用。
Vostok Press代表金贤浩(音)的见解与他有所不同。作为摄影媒体的出版人兼照片评论家长期活动的他,非常关注所谓照片的媒体属性的变化。他说道:“铃木达朗也好,富士胶片也好,应该都很震惊。他们不可能不了解摄影文化。他们一定是在自己的常识下完成这个摄影项目的,但突然间就出了问题。摄影变了。因为摄影的性质比起图片本身,放在图片上的支撑体规定得更大。只有一张银版照片的时候,和可以无限制地复制时,还有像现在数码照片无法知道其复制和流通的轨道时,照片的性质不可能一样。”如果世界变了,人们的感觉也会变,对恐惧的感觉也是如此。以前看起来平凡的照片如今可以引起恐惧,照片的普遍性和杀伤力以几何级数增加多少,大众可以容忍的街头摄影的范畴就会变得窄多少。根据时代的变化,变得开阔的艺术领域和逐渐变窄的艺术领域乍一看来理所当然的命题。只是金贤浩所想的变化并不止于此,他认为街头摄影的存在价值也发生了变化。他表示,“在公共场所拍摄的权利优先的方向制定法律时,是因为那一方有了更社会性便利的缘故。但是我现在质疑这样的便利是否还存在。主张摄影担任记录和举报角色的主张,已经有太多的照片。即使依旧有便利性,相比之下普通市民的权利受到太大的侵害。也就是说,支撑街头摄影存在的道德依据正在消失。我认为,伟大的街拍时代已成为过去的可能性更大。“金贤浩还表示,作为喜欢看摄影作品的人,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这只是个人的想法,摄影家们要做的就是在时代有限的条件里思考什么是可能的?
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从很多受访人员口中听到了“我也很好奇的结论”这样的话。在法律界人士和文化、艺术界人士截然不同的主张下,谁都不可能做出出色的回答。其实铃木达朗受批评的照片背后有着小秘密。在汉堡旅行的铃木达朗在街上碰到一群青年并交谈,然后他举起相机时镜头前的男人伸手指着喊“别拍我,照我的朋友,他比我更上镜。”严格来讲这张照片的拍摄对象不是陌生人,认识到拍摄进行与否并默认许可。非要选择这张照片的编辑部内部,肯定也与铃木达朗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本文倒不是为铃木达朗做辩解。个人的认同感、对信息保护的范畴和照片与视频的艺术特性,或者对公共性和自由的关系,分析也许有些不足。对街头摄影价值和界限的看法众说纷纭,我们更需要立体的理解和哲学的理解。这也是为了形成新的摄影艺术基调。在变得那么悲壮以前,读这篇文章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摄影师,,也都是拍摄对象,应为都生活在消费者时代。
注:铃木达朗1990年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富士通工作,2014年5月辞职离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富士通,对于一个已49岁有家庭的男人,这是一个绝不容易的决定。他不是因为赚了很多钱,日后可以生活无忧而提早退休。他是为了追求摄影理想而提早退休。当时他表示:“我想过,如再给我一次,我也会希望为自己的人生搏一搏。就算世俗人觉得我的决定是一件如何傻的事;就算有99%失败的机会,只有1%成功的机会,我都会把所有希望放在这1%里面。有可能我会失去一切,但我不会后悔。我认为人生若没有挑战,每日都在原地踏步状态生活,这样子的的生活才会令我有悔今生。”【飘在思密达原创 图片版权所有】
【飘在思密达2020专题系列一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首尔地铁】(点击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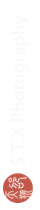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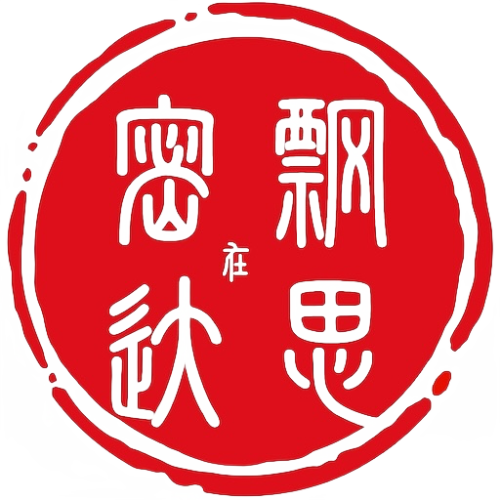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