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泛滥 喜也悲也?
飘在思密达在日记本上摘抄过这么一段话:在这个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为了信息的生产者。而人们不经大脑给出的轻率意见,可以瞬间淹没任何理性的声音。
今年初,法国足坛名宿亨利宣布退出社交媒体,直至这些平台能够像对待侵犯版权那样严厉打击种族主义和欺凌,规范平台的内容。他表示,“种族主义、欺凌行为、以及对个人造成的精神折磨,这些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以至于不能被忽视,平台必须承担起责任。如今创建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太容易了,在那上面可以匿名欺凌和骚扰他人,却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亨利曾效力过阿森纳和巴萨等豪门,他的Instagram账号有270万关注者,Twitter账号有230万关注者,而Facebook账号则有1000万关注者。
差不多的时间,还有一件事。著名作家阎连科荣获了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他在颁奖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的获奖感言,引起很大的争议。虽然他表达的中心意思就是反战、人性、和平,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与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都不会超过爱,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借题发挥。
诚然,没有一家社交媒体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事实和新闻,是不带有情感和价值判断的。但当每一个人都拥有了一台具有拍照与录像功能的手机之后,信息的生产机制已经彻底被颠覆掉了。生产者更多关心的是流量,不少已经不会再三再四地强调真实性客观性平衡性,受众群体也更多关心的是生活、八卦、娱乐、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个个抖音YouTube上的“平民英雄”,一步步取代寒窗十年的社会精英,喜也?悲也?崛起是喜,泛滥是忧!
飘在思密达曾经采访过阎连科,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也就是个随和的邻家大叔而已。所谓树大招风吧!
附采访原文:
2019年11月,阎连科受韩国大山文化财团邀请,在首尔出席“2019与世界作家对话”活动。阎连科的作品《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年月日》、《风雅颂》、《四书》、《夏日落》、《坚硬如水》等都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丁庄梦》尤为受到韩国读者喜爱。
►您在延世大学的演讲中提到在军队二十几年,这个经历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帮助?
阎连科:26年,有非常大的帮助。军队是相当重视文学、文化的地方,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不断举办各种创作学习班。参加学习班,参加讨论,还有人帮忙修改稿子,获得非常多的帮助。此外,在军队我才真正打开阅读的大门,才知道原来《飘》这么好看,才知道原来《安娜·卡列尼娜》也这么好看。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根本不会有今天的阎连科。
►您获得过国内外重量级文学奖项,也可能是下一个获诺奖的中国作家。据说日本文学界只关心中国三位作家:莫言、阎连科和残雪,您怎么看?
阎连科:媒体讲诺贝尔文学奖,纯粹是为了媒体的热闹。任何人不真正了解评奖的内幕,怎么提名?怎么评选?其实就是一种游戏。一个作家最终要做的,是要写出满意的作品。获奖,都是人生的偶然,是天上掉馅饼。在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或者欧洲也好,我的作品也许相对来讲比其他作家翻译的多一点点,多受欢迎一点点,并不能证明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只是我的机遇稍微好一点。中国有很多好作家,其他作家遇到相同的机遇,他们的作品也会被翻译很多的。
►您在讲座中说还有五到十年的创作时间,此前也曾讲过写到65岁这样的话,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阎连科:倒不是说70岁了就一个字不写了,而是我认为要创作出好的作品,过了那个年龄基本上就不大可能了。未来五到十年时间里,希望我可以写出自己满意的长篇作品。写不出来的话,写作的人生就真的这么结束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没有独一无二的作品,就是一个失败的写作者。文学创作和其他艺术创作比方绘画或书法是不同的,作家都有一个创作的黄金年龄,而画家或书法家基本都是年纪越大功力越深厚,作品也更有价值。
►现在创作的门槛降低,网络文学流行,网络作家崛起,很多年轻人也都是通过电子产品看书,您怎么看?您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阎连科:我对网络文学接触的比较少,这是新型的写作形式,而我是相对老派传统的。或者说我觉得文学最终还是要归位人性、审美等艺术元素,归为实践,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文学。各种文学的产生都是正常的,毕竟现在的时代也不是单一的时代。
创作的门槛降低,是面对公众发表的门槛低到近乎没有,不需要像以前一样白纸黑字印出来,现在可以发布到网上。但是,我认为也许谁都可以拍电影,谁都能写小说,但好的电影、好的小说,它的标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我还是坚持用笔写,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坐下来写两到三个小时,写个两三千字。然后可能看看NBA,下午会客,看看书。在北京应酬比较多,在香港就相对安静一些。
►您喜欢NBA哪个球队?
阎连科:现在喜欢的球队都乱套了,勇士队球员伤病多,垮掉了;火箭队也乱,国内也不报道了,一片混乱。
►您在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跟很多年轻的作家打交道,最大感受是什么?
阎连科:我的最大感受是现在的青年作家读书远比我们多,范围也广得多。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八九十年代读了不少书,现在也坚持读一点,但还是比不上他们。我所熟悉的80后、90后,读书都非常多,非常了不起。读书是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不读书无法谈写作,短时间也许可以应付,但坚持不了很长时间。这代年轻作家,是会产生伟大作家,写出伟大作品的。
►对年轻人的阅读和写作有什么建议?
阎连科:多读书是好事情。中国是盛产故事的国度,结合一下人生经验、社会经验,如果又读了很多书,真可能写出惊人的作品。
►您的创作动力是什么?素材都来源自哪里?有没有遇到瓶颈期?
阎连科:我到目前基本上没有遇到瓶颈期,因为人生经历太丰富,可以写的故事很多。好比一堆钻石让你挑一颗,反而不知道怎么办?回到农村坐到饭桌上,满桌都是好小说。要说有困难,也许是找不到最独特的写故事的方法。创作动力也许就是我说的,我一直想写一部不是小说的小说。写了,觉得不行,过一段时间,又想尝试。尤其是长篇小说,每次写完,总能发现问题。就是带着侥幸心理尝试创作,也许这次可以写出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这是最大的原动力。
►您怎么看被封“荒诞现实主义大师”这个称号?
阎连科:我不是什么大师!也不荒诞!我可能是另一种现实主义,或者是来自真正的现实主义。每个人看到的现实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看到的是这种,那我看到的可能是另一种。14亿人口,南方北方,每个人的入口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评论家把您和鲁迅作比较,您怎么评价鲁迅?怎么评价您自己?
阎连科:那是把我捧到天上去了,鲁迅堪称我的半个灵魂。鲁迅的伟大,思想的伟大,小说的语言,都不是我们能够比的。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只是中国作家中相对勤奋的一个,也有些幸运的一个人。我的幸运就是说,遇上四十年改革开放好时期,有的作品也许有争论,但正常的生活有保障,可以安心创作。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把作品写好,我认为我是幸运的。
►您最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对韩国的文学作品、作家了解的多吗?
阎连科:我更多会喜欢一些国外的作家或作品,但一直在变,每过三五年就会变。因为创作需要不断变化,喜欢的作家或作品也就会变化。
对韩国了解的不是很多,零零碎碎地会读到一些作品,感觉写得非常好。回国前要跟几位韩国作家座谈,其中有一位80后作家叫金爱烂,看过她的两部小说。还有韩江的《素食主义者》,也写得非常好!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阎连科的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出版,并在国内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重要奖项。2014年5月27日,阎连科凭借捷克语版的《四书》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 ,成为继村上春树之后第二个获得该奖项的亚洲作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他被称为继莫言后最接近诺奖的中国作家,也被称为“最有争议的中国作家”。纽曼华语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美中关系研究所在2008年设立,旨在表彰华语文学领域的杰出作品。阎连科曾于2009年、2015年和2017年三度被提名该奖项,现今成为莫言、韩少功、王安忆之后第四位问鼎纽曼文学奖的中国大陆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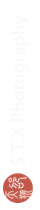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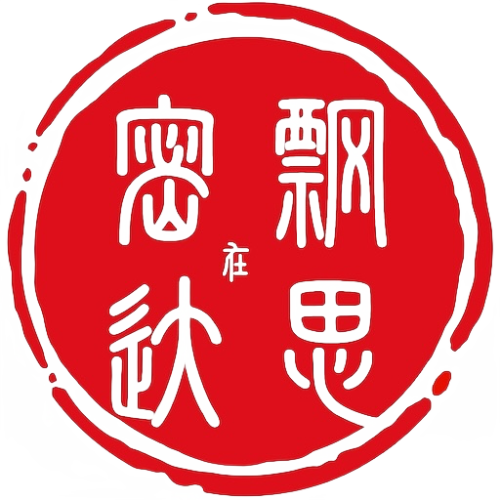


近期评论